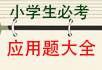第2期 | 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
2017-08-07 17:29
来源:新东方网
作者:于慈江
(一)
好的诗作为精神食粮,无论出自于何时何地何人,都应该也一定会有益于世道人心,有益于夯实人们生存的精神信念,有益于矫正人们的精神匮乏与畸曲,有益于提升人们登临或期许的精神高度——这既是一首好诗的底线,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作为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,波兰当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(Adam Zagajewski)的诗就既能予人以高质量的审美享受和知性愉悦,也能使人充分感受到,虽然世界不免混乱、邪恶,生活可能过于粗粝、让人压抑,但并非不值得在每个早晨为之而醒来。
且看他的一首诗《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》(Try to Praise the Mutilated World):
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。
别忘了那长长的六月天,
以及野草莓、葡萄酒和露水。
还有那些荨麻,不枝不蔓
长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。
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。
你望着那气派的游艇和轮船;
其中一艘有着长远的前程,
而其他的注定在咸腥中湮没。
你曾见过走投无路的难民,
你也听到过刽子手们欢歌。
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。
还记得那些时辰,我们一起
待在白房子里,窗帘飘动。
冥想重返乐声骤起的音乐会。
你秋天在公园里采集橡子,
而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飞旋。
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,
连同画眉鸟掉落的灰色羽毛,
以及那柔和的光,
它迷失、消散复又折返。
于慈江 译
扎加耶夫斯基这首乍看并不如何打眼的诗其实非常有名,光是黄灿然等给出的汉译版本就多达五、六种——该诗李以亮、乌兰、黄灿然以及姜海舟的汉译诗名分别为《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》《你试着赞颂残缺的世界吧》《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》《尝试赞美这残损的世界》。
如上所示的此诗译文由笔者本人译自英文(‘Try to Praise the Mutilated World’ by Adam Zagajewski, From Without End, published by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2003),还是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。
譬如,在原诗第四、五两行The nettles that methodically overgrow / the abandoned homesteads of exiles中,副词methodically被不同的译者依照最基本的字典义项,分别比较省事、比较书卷气地译成“有条不紊地”(乌兰)、“有条理地”(黄灿然)和“井然有序地”(李以亮)。笔者以为,还是不妨从植物本身的属性着眼,将这个副词“将植物就植物”地就译成“不枝不蔓地”,将这两行就译成“还有那些荨麻,不枝不蔓/长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”为好。因为人们通常说一个东西很枝蔓,是说它条理性差;说它不枝不蔓,则是比较有条理的意思。荨麻本身作为蔓草可到处蔓延,却居然能不枝不蔓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——这样一种更为直观的悖谬更具冲击性,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也更大一些。
再譬如,原诗第七行You watched the stylish yachts and ships中的形容词stylish被分别译为“优雅”(乌兰)、“时髦”(黄灿然、姜海舟)、“漂亮”(李以亮)。笔者以为,考虑到它所修饰的是体量巨大、不乏气势的游艇和轮船,还是译成“气派”来得更为恰切和精准。
又譬如,原诗第九行while salty oblivion awaited others被分别译成“只有带盐味的虚无等待着其它船只”(乌兰)、“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”(黄灿然)、“另外的,带咸味的遗忘等着它们”(李以亮)、“而咸涩的湮没等待着剩下的”(姜海舟)。问题之一是,无论将片语salty oblivion译成“带盐(咸)味”的“遗忘”还是“虚无”,都不仅有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含义之嫌,也不免让人费思量——究竟什么是带着盐咸味的遗忘或虚无?不带盐咸味的遗忘或虚无该又是什么?
其实,与“遗忘”这一义项相关联,oblivion还有“埋没、湮没、湮灭”的含义,一如姜海舟所译。而salty除了意指“(含)盐的”或“咸的”之外,还有“海洋的、海洋生活(气息)的”等含义。所谓salty oblivion,无非是“在海洋或海洋的生活(气息)中湮没(灭)”。笔者因此将这一片语径直译成“在咸腥中湮没”——所谓“咸腥”,正是海洋独有的气息。姜海舟的“咸涩的湮没”与此较为接近。
问题之二是,若是过于拘泥于原诗的字面意思和语序,反而会使所译过于欧化,读或理解起来不免多少会有些别扭——所谓“等待”(awaited)无非意指命运无可逃避的规定性、注定性。故而,将整句译成“而其他的(船只)注定在咸腥中湮没”不仅顺理成章,也更其自然和易解。
然而,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首《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》之所以会暴得大名,主要是因为它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恐怖袭击之后不到一星期,就被《纽约客》(The New Yorker)杂志醒目刊出——这一期的《纽约客》杂志虽然发行日期标注的是2001年9月24日,却是在9/11恐怖袭击之后不到一个星期(大概是9月17日)提前印发的
[详见After 9/11: An E-Book Anthology by The New Yorker, August 19th, 2011(http://www.newyorker.com/news/news-desk/after-
911-an-e-book-anthology)]。
该诗通过呼吁包容一个有缺欠的世界,通过期许一个有希望的未来,诗意地填补了温抚9/11事件之后美国普遍存在的心灵创痛这一空白——据《纽约客》诗歌编辑称,扎加耶夫斯基此诗的英译2001年一经在美国发表,便引起极大反响,不仅在网上被广泛传播,也被很多单位贴在告示栏上,被很多家庭贴在冰箱的门上(详见Cynthia Haven, Risk, Try, Revise, Erase, Poetry Foundation, April 17, 2006)。
不过,据扎加耶夫斯基在美国接受采访时披露:他这首被美国人青睐的诗并非直接受9/11事件触动而作,而是写于约一年半之前的欧洲,在波兰或德国的火车上;他所说的“残缺的世界”(the mutilated world),首先是指他自己儿时的世界——记忆所及的孩提时光田园诗般朴质宜人,而所处的环境却又的确并不让他愉快(详见John O’Rourke, Famed Polish Poet Adam Zagajewski Reads Tonight, BU Today, 09.15.2010)。
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诗不乏美好的意象,譬如“那长长的六月天/以及野草莓、葡萄酒和露水”,还有“公园”“橡子”“白房子”“音乐会”和“柔和的光”等。它也并未回避令人不免心寒、不免黯然神伤的严酷现实——“流亡者废弃的家园”、得意的“刽子手”和“走投无路的难民”。诗人想把世界的本相及其复杂性展示出来:作为一种随意蔓生的蔓草,荨麻偏偏能把流亡者废弃的家园弥漫得不枝不蔓,实在不免有些意味深长;世界的残缺一如鸟的褪毛掉羽和光的明灭闪烁、飘忽不定,需要人们以平常心淡定面对,而不是一味地沮丧或愤世嫉俗;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可怕,人们身边不起眼的小事都能充满意义地让它值得赞美、珍惜和不轻言放弃;那一缕虽微弱但却无处不在的柔光不论多么闪烁不定、不易捕捉——哪怕珍稀得一如吉光片羽,毕竟还是光,还是希望。
(二)
扎加耶夫斯基这首《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》虽然意蕴深远、富含张力,不拘执于对生活表象的简单描摹和体味,但还是透过对“流亡者废弃的家园”与“走投无路的难民”的人文关怀,触及了放逐或出走、流放或流亡这样一个既敏感又恒常的诗歌主题。
在他2003年出版于美国的诗集Without End(《无止境》)中,直接间接、或隐或显地涉及这一主题的诗包括但不限于《游船》《漫游者》《流亡者之歌》《会有一个未来》《给我自己,在一本相册里》《在陌生的城市》《旅人》《休斯敦,下午六点》等(详见李以亮译:《无止境:扎加耶夫斯基诗选》,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15年版)。
就其悲壮、惨烈或决绝的质地而言,放逐(流放)和出走(流亡)本质上并无二致——无非前者出于被动,后者出于主动而已。当然,当事者双方心照不宣、半推半就的居间状态也时有出现,且愈益普遍。而无论是放逐还是出走,流放还是流亡,作为艰难蹀躞或迂曲跋涉的人生姿态,都骨子里可以与on the road或“在路上”这三个充满姿势感的打眼字眼对接。
作为不预设目标的一种陌生化体验与追寻,作为追求心灵极致自由的一种暗示性意念与决心,既是精神灌注又体现为直觉行为的“在路上”早已超越了约60年前美国小说家兼诗人杰克·凯鲁亚克(Jack Kerouac,1922-1969)同名小说设定的具体语境和文化氛围——按作者郑重其事的解释,是“两个天主教伙伴漫游整个国家寻找上帝的故事”(笔者转译自Fellows, Mark, The Apocalypse of Jack Kerouac: Meditations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, Culture Wars Magazine, November 1999);按当时众多读者的印象式解读,是几个穷极无聊、无所事事者一起外出寻求刺激的故事,成了绝不从众、“一意孤行”、义无反顾的独标异彩或前行姿态的一种象征。
纯从诗歌的视角来看,所谓“在路上”,就是诗人杨炼所谓“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,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”,“永远出发,却永无抵达”(杨炼:《什么是诗歌精神?——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》);就是通过目的虽模糊却充满希望的执着行路与决不妥协的艰苦行吟,咀嚼历史的辽远与时空的味道,对抗现实的压迫与精神的腐蚀,获取直觉与体验的精神力量,搜寻新鲜的语感与诗意的颖悟或温暖。
而作为“在路上”这一永不妥协的不断前行姿态的极致性表现,诗歌的去国或出走古今中外就从未断绝过。譬如,已故波兰诗人米沃什(Czesław Miłosz,1911-2004)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走,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在80年代初出走,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(أدونيس)在50、60和80年代多次出走,以北岛和多多等为代表的相当一批中国当代诗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走……
诗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流浪或智性走神,而诗歌的出走国门与其说是迫于情势或现实压力,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自觉或宗教式苦行;与其说是要更好地获得世界性视野,毋宁说是要有现场感地置身于一个他者场域,更好地反观自身的历史与现实。
因为,想获得国际性视野不一定非得走出国界,在异域生活——当代实力派诗人西川始终在中国大陆写诗和生活,却绝不乏国际眼光,就是一个显例。
对于流落他乡或出走国门的两难、凄楚、无奈乃至宿命性,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句“外部不是我家园,内部于我太狭窄”(转引自姜妍:《阿多尼斯:自由地表达,才是我的祖国》,《新京报》2012年10月25日)鞭辟近里,堪称最形象具体也最简约精当的归纳与刻画;对于诗歌出走的本质,波兰诗人、诺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有过非常精辟、道地的解说[全小虎译:《历史、现实与诗人的探索——米沃什访谈录》,节选自法国《文学杂志》1987年10月号,红岩文学微信(http://chuansong.me/n/663932)]:
我在哈佛大学作报告时,曾指出:一个波兰诗人无论住在哪里,其真正寓所是他国家的历史……因为他并不是通过空想去揭示人的条件,而是在某个时代、某个地域范围实现这一意图的。
这意味着,米沃什虽然长期去国,甚至最终为环境所迫改换国籍,成了所谓美籍波兰人或波兰裔美国人,但他却始终活在其祖国波兰的语言与历史当中。诗歌的出走在他这里实质上是出而未走,变而未离其宗。套用阿拉伯语诗人阿多尼斯的名句“我的祖国是阿拉伯语”(详见姜妍:《阿多尼斯:自由地表达,才是我的祖国》,《新京报》2012年10月25日),波兰诗人米沃什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:“我的祖国是波兰语!”
而本文前面细读过的《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吧》这首诗则暗示人们,很大程度上,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把整个世界理解为一个大的流亡或放逐场域。
他在自己的另一首诗《读米沃什》中,把前辈诗人米沃什概括为“无所不知的富人”“无家可归的乞丐”“形影相吊的移民”(参见于慈江:《诗歌:出走与打起精神》,《世界文学》2015年第6期,第163页)。这正是精神高贵、知识淹博、流离失所、孤独落寞的去国出走者的标配(“无所不知的富人”一句以学养淹博为富,指的主要应是诗人精神上的尊贵),也实际上可视为扎加耶夫斯基本人自况。
以这一理解为基础,与其说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是叛逆、冷漠、嫌憎厌弃,毋宁说是谦卑、热诚、悲天悯人。或者说,他将自己的或诗歌的出走理解为一种命定,归结为一种天然——他不过是顺势而起、应命而为。
这正是他在讨论或面对这一出走时的态度低调之至、冲谦之至的根本缘由。这也就难怪,扎加耶夫斯基笔下的野草莓、鸟羽与柔光不仅鲜活、有亲切感,也在不无缺憾和悲凉感的同时,显出其正向、优雅、值得赞美的一面。